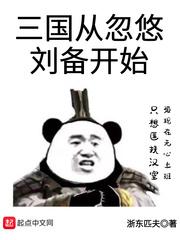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572章 静默消亡(第2页)
纸上没有称谓,没有落款,没有任何多余的字迹。只有一行用黑色中性笔写下的、清晰而冷静的句子:
“你成功了。”
字迹是林静的,娟秀,平稳,力透纸背。每一个笔画都像一根冰冷的钢针,狠狠扎进李伟的眼球,然后穿透颅骨,直刺进他混乱一片的大脑。
成功了?什么成功了?
他茫然地捏着那张纸,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。脑海里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,轰然巨响后只剩下飞沙走石的碎片。那些被他刻意忽略、被粗暴压制的声音和画面,此刻裹挟着迟来的巨大力量,疯狂地倒灌回来。
---
记忆的闸门被“你成功了”那四个冰冷的字眼轰然冲开,碎片呼啸着,带着令人窒息的尖啸,将李伟拖回十年前那个同样闷热的夏夜。
那时,他的公司刚拿下第一笔像样的订单,庆功宴喧嚣散场,他带着一身酒气,脚步虚浮地推开家门。客厅只亮着一盏壁灯,昏黄的光晕温柔地笼罩着蜷在沙发上的林静。她穿着柔软的棉布睡裙,膝上摊着一本厚厚的《财务会计实务》,脑袋却一点一点,小鸡啄米般打着瞌睡。听见门响,她猛地惊醒,眼中瞬间漾起明亮的欢喜,像投入石子的湖面,碎光粼粼。她赤着脚跳下沙发,小跑过来,带着一股淡淡的、令人安心的皂角清香。
“回来啦?累不累?”她自然地接过他搭在臂弯的外套,仰着脸看他,眼神里是毫无保留的、近乎崇拜的关切,“我给你煮了醒酒汤,一直温着呢。”那声音像浸了蜜糖的羽毛,轻轻拂过他被酒精灼烧的神经。那时的她,像一株缠绕着他的常春藤,温顺、依赖,满心满眼都是他李伟的影子。她的世界,似乎就是以他为中心旋转的星系。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仰望的星光开始熄灭、变冷的?
记忆的画面粗暴地切换。五年前的一个傍晚,夕阳的余晖将客厅染成一片倦怠的橙红。林静坐在餐桌旁,手里捏着一份文件,脸上带着一种久违的、小心翼翼的兴奋。她清了清嗓子,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期待:“阿伟,公司……财务部的陈姐快退休了,主管的位置空出来……我们经理今天找我谈了话,意思是……想推荐我试试。”
李伟正瘫在沙发里,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不耐烦地划拉着当天的球赛新闻。闻言,他眼皮都没抬一下,鼻腔里发出一声短促的、带着浓重鼻音的“呵”。那声音像淬了冰的针。
“你?”他嘴角向下撇出一个刻薄的弧度,终于舍得把视线从手机屏幕上移开半寸,斜睨着餐桌旁那个瞬间僵住的身影,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轻蔑,“就你?管好家里这点事儿就得了,瞎凑什么热闹?女人家,心别太野。升了主管,加班应酬少不了,谁给我做饭?谁管孩子?别到时候手忙脚乱,家里一团糟,还得我给你收拾烂摊子!”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锥,精准地刺向她刚刚鼓起的一点勇气。
林静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,捏着文件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。她张了张嘴,似乎想说什么,嘴唇翕动了几下,最终却只是紧紧地抿成了一条苍白的直线。眼中那簇因期待而燃起的小小火苗,在他鄙夷的目光和冰冷的言辞下,迅速地黯淡、熄灭,最终沉入一片深不见底的死寂。她默默地垂下眼帘,盯着手中的文件,仿佛要把它盯穿。几秒钟死一般的沉默后,她一言不发地站起身,把那份承载着她短暂职业梦想的文件,轻轻地、却无比沉重地,塞进了旁边书柜最底层的抽屉深处。抽屉合上时发出的轻微“咔哒”声,像一声无言的叹息,也像一道沉重的门,在她身后缓缓关闭。
“不识抬举!”李伟看着她顺从(或者说麻木)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,心里甚至掠过一丝“为她好”的、荒谬的满足感。他觉得自己成功掐灭了一次不切实际的“野心”,维护了家庭应有的秩序。她后来果然没再提过这事,仿佛那个小小的插曲从未发生。李伟把这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“懂事”,一种对他权威的顺服。
然而,这只是漫长侵蚀的开始。
时间又跳到一年半前那个深秋的深夜。刺耳的手机铃声骤然划破卧室的沉寂。李伟烦躁地翻了个身,迷迷糊糊摸到床头柜上震动的手机。屏幕上跳动着“爸”的名字。他睡意正浓,想也没想,直接按了拒接,顺手把手机调成静音塞回枕头底下,嘴里含糊地咕哝了一句:“烦死了,大半夜的……”随即又沉沉睡去。
他完全不知道,也根本不想知道,电话那头,是林静远在老家县城医院走廊里焦急的父亲。老人突发心绞痛,情况危急,母亲六神无主,只能一遍遍拨打女儿女婿的电话。林静的手机,因持续不断的拨打,电量早已耗尽,自动关机。
第二天,李伟被客厅里压抑的抽泣声吵醒。他揉着惺忪睡眼走出去,看见林静蜷在沙发一角,肩膀微微耸动。她抬起头,眼睛红肿得像核桃,脸色苍白得吓人,声音嘶哑得几乎不成调:“我爸……昨晚进医院了……差点……差点没救过来……妈打了我们好多电话……”她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,那里面翻涌着绝望、后怕,还有一种李伟当时无法理解、也不愿深究的,近乎冰冷的质问。
李伟心头掠过一丝极其短暂的不安,随即被更强烈的、被扰清梦的恼怒所取代。他皱着眉,不耐烦地挥挥手:“行了行了,这不没事了吗?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!你爸身体本来就不好,有点风吹草动就大惊小怪!再说,你老家那么远,我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?飞回去啊?净添乱!”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,转身走向厨房,“赶紧弄点吃的,饿死了。”
他甚至没有走过去,哪怕象征性地拍一下她的肩膀。他错过了她瞬间攥紧的拳头,和眼底最后一丝微弱的光彻底湮灭的瞬间。从那天起,林静似乎真的“懂事”了。老家再有任何事情,哪怕父亲复查、母亲住院,她都再没在他面前提过一个字。她只是默默地在某个周末收拾行李回去几天,又默默回来,像完成一件与这个家、与他李伟毫无关系的例行公事。李伟乐得清静,甚至把这视为她终于“明事理”的表现。他成功地将一个“麻烦”隔绝在了他的世界之外。
而最终引爆一切的,是半年前那个暴雨如注的深夜。
窗外电闪雷鸣,狂风将雨水疯狂地砸在玻璃上,发出密集而骇人的声响。李伟正和几个生意伙伴在豪华KtV包厢里推杯换盏,烟雾缭绕,音响震耳欲聋。他喝得兴起,手机被随意地丢在沙发角落,屏幕明明灭灭,不知疲倦地显示着同一个名字:林静。
他瞥见过一次,但震耳的音乐和朋友的起哄让他毫不在意地划掉了。“又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。”他心里嘀咕着,很快又被新一轮的敬酒淹没。他甚至带着点隐秘的快意,想象着她一遍遍拨打无人接听的电话时,那副无助又不得不忍耐的样子。这种掌控感让他无比受用。
他完全不知道,就在此刻,城市的另一端,他们的儿子小磊正发着高烧,小脸通红,浑身滚烫,呼吸急促。林静抱着滚烫的孩子,在小区门口暴雨肆虐的街道边,徒劳地一次次挥手,试图拦下一辆空驶的出租车。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浇透了她单薄的衣衫,顺着发梢流进脖颈,刺骨的寒冷。怀里的孩子烧得迷迷糊糊,发出难受的呜咽。一辆又一辆的车飞驰而过,溅起肮脏的水花,打在她身上。
她一手紧紧抱着孩子,一手徒劳地举着早已没电自动关机的手机,徒劳地试图拨号。雨水顺着她的脸颊疯狂流淌,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绝望的泪水。在又一次被疾驰而过的车辆溅了满身泥水后,她终于放弃了。她死死咬住下唇,直到尝到一丝血腥的铁锈味,用尽全身力气抱紧怀里滚烫的小身体,毅然决然地转身,顶着瓢泼大雨,一步一步,艰难却无比坚定地朝着最近的医院方向走去。每一步都踏在冰冷刺骨的水洼里,也踏碎了她对这个家、对那个男人的最后一丝残存的、名为“依靠”的幻影。
当李伟带着一身酒气和廉价香水味,心满意足地回到家时,已是后半夜。家里一片死寂,只有客厅一盏小夜灯散发着微弱的光。他看到林静卧室的门紧闭着。他蹑手蹑脚地推开门,借着门缝透进的光,看到林静侧身躺在儿子小磊身边,一只手还轻轻搭在孩子的额头上。她的头发半湿着,贴在苍白的脸颊上,眼下一片浓重的青黑。孩子似乎已经退烧,呼吸平稳了许多。
李伟心里莫名一松,甚至带着点“虚惊一场”的侥幸,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。他完全没注意到,或者说根本不在意,林静在他推门的一刹那,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,搭在孩子额头上的手指微微蜷缩,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自始至终,她没有睁开眼,没有发出一丝声音。那无声的抗拒和冰冷的距离感,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哭闹都更令人心寒。
快穿:反派独宠小可爱
快穿1v1甜宠自从神魔大战以后,天宫上的人都知道小仙女阿司养了一条小黑龙。那条小黑龙可娇气了,不仅吃饭要喂,就连睡觉也要抱着。直到,小黑龙长成了大黑龙。他把阿司推下了轮回台,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。阿司,你不要我了吗?阿司,你抱抱我后来的后来,阿司轮回归来。魔尊上渊马不停蹄的杀上了天宫。阿司你出来,我...
超暖总裁爱不够
整个云州市的人都知道苏家有个臭名昭著的二小姐,没人愿意娶。苏子悦只好自己找人求嫁,好不容易嫁出去了,老公却是个三无男人,房子没有,车是借的,存款就不要问了,怕伤人自尊。可是,三无老公摇身一变,成为了响当当的欧洲金融大亨L.K集团的总裁,绝对的有钱有权的大人物,苏子悦一脸懵逼。你说你没房子?在云州市没有。你说车是借的!哦,那辆车我后来送给手下了。苏子悦怒了骗子!离婚!秦慕沉危险的眯起黑眸不负责你想白睡?苏子悦秒变怂货不不敢...
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
汉灵帝西园租官,要不要租?租!当然租!因为只要恰好租到灵帝驾崩前的最后一个任期,就等于直接租房租成了房东!租官租成了诸侯!所以,匡扶汉室怎么能只靠埋头苦战...
我居然是这种身世
被女友甩后,周小昆接到了老爸的电话儿子啊,咱家其实有座矿,你是个富二代啊!穷了二十年了,原来自己是个富二代,周小昆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...
霍延西宋叶
王者之路张牧简介主角张牧李晴晴穷是一种病,我得了十年的绝症,直到那天我爸出现,让我百病不侵!一个寒门出生,如何才能继承世界第一家族罗斯柴尔德!...
女主她不想吓人
南山每晚总有两个小时,灵魂会附到相识人的物品上。有一天晚上,她成了男友的手机。结果半个小时前对她道过晚安的人,正在和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聊天。在听清楚他们明天的约会时间地点后,她让手机强制关机了。南山呵呵,不想听你们谈情说爱。一年后,南山与某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某人兴致勃勃,诱哄道要不要先验货?南山不用。穿成他家花洒的时候,就把他有几块腹肌都数的清清楚楚这种事情她会说?...